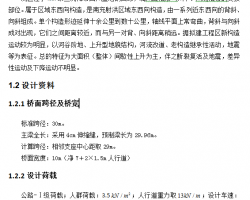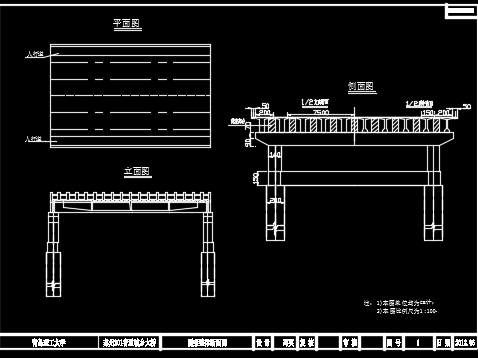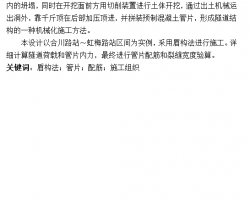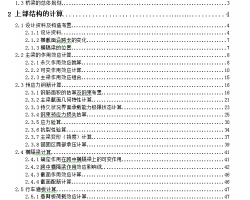回顾了美国城市轨道交通项目评价方法的主要特点及基本原理,重点对UMTA评价方法的发展变化过程进行了综述,分析各个时期UMTA评价方法的特点。从中可以看出美国在进行城市轨道交通项目评价时的思路、价值取向、评价指标及存在问题,这对改善我国现行的评价方法有借鉴作用。
在未来的5至10年,我国城市轨道交通建设将以超常速度发展。由于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各类建设很多,建设资金相对紧缺,这就需要应用项目评价方法对轨道交通建设项目的建设时机、建设方案进行综合比较和筛选,以便取得良好的投资效果。目前,我国城市轨道交通建设项目预可行性研究及工程可行性研究中已有一套项目评价方法,但这种方法仍然有一定的局限性,其评价指标及评价方法尚待改进。
我国城市轨道交通建设体制与美国等发达国家有很大差别,但是,随着我国加入WTO,城市轨道交通领域可能引入国外投资,相应的项目评价方法也应适应国际化发展的要求。本文试图综述美国,尤其是UMTA(urbanmasstransportationadministration,城市轨道交通管理局)在城市轨道交通项目评价方面的发展状况及特点[1~3],为改善我国城市轨道交通项目评价方法及提高评价水平提供借鉴。
1交通项目评价方法的回顾
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20年代,美国各类运输项目的投资决策、票价优化及政策制定等一直沿用欧美经济学家提出的保本分析法。早期运输经济学的发展是建立在效率概念的基础上。经过几十年的相对沉寂之后,交通运输经济学家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改进交通经济分析方法,主要有经济效果法和费用-效率分析法,从而可以更好地评价交通供给、交通需求及其平衡关系,较合理地确定票价和投资水平[4].相比而言,费用-效率法在各类期刊中出现得更多。
1.1费用-效率法
1978年,Fielding等人[5]提出了9项评价交通项目的指标,其中3项反映效率,4项反映效益,还有2项两者兼有。效率指标与各个城市当时的发展目标密切关联,因而具有较强的地方及时间特征。由于这种指标系中不包括资本成本,因而对投资者(公司、财团等)的资金优化配置不能起指导作用。
1981年Horn曾收集9个具有轨道交通的发达国家大城市(其轨道交通运量分担率为2%~40%)的费用-效率法评价指标,发现它们之间存在很大差异[6].他不赞成使用费用-效率法,因为其指标的标准化是很难办到的。他认为,没有一套指标体系能够公正地评价美国各城市的轨道交通项目。Stokes认为,在轨道交通系统选择时应当主要考虑各城市的具体发展目标[7].UMTA不赞成这种观点,因为没有一个统一的评价指标系,就不能有效、公正地进行联邦政府对城市轨道交通的投资决策。
构建一个具有广泛适应性的评价指标体系,难免会引起指标的相互交叉和重叠。为此,有人提出了归并为单一指标的做法。1980年伦敦交通运输部使用单位总成本的客运周转量来评价交通系统的改善效[8].1984年Forkenbrock[9]提出单位投资增量所引起的旅客增量这一指标。这种做法虽然能够简化评价过程,对备选方案加以筛选,但是不能直接度量整个项目的经济效益总量变化,因而不能得到项目投融资者的支持。
1.2经济效果法美国有关交通规划的教科书普遍建议同时使用费用-效率法和经济效果法,费用-效率分析法对地方的项目评价较为适用,但是国家政府的投资分析应该采用经济效果法,即使经济净现值取得最大值。
轨道交通项目一般有两个目标:净现值的最大化;设备利用的最大化。这就要求评价中对各种影响效果,例如居民的迁移、低收入乘客、空气质量等进行量化,甚至包括社区目标的量化。在评价指标中应该包含经济福利的因素[1].
2项目评价的基本原理
2.1经济理论
轨道交通项目,属于公用事业,在理论上可以通过比较其替代方案的经济成本和效益来进行评价。一般来说,项目目标就是要使净效益最大化,即将整个项目在工程寿命期内的成本和效益均被贴现到基年(项目立项或开工时),其贴现率应合理地体现社会对资金的时间成本及资本金的机会成本。
交通项目的直接成本是预计的建设费用和运营费用,间接成本是指如空气、噪声污染等额外影响造成的费用。直接效益包括运营收入、出行时间的节省、从其它交通方式转移过来的乘客所避免的交通事故等。间接效益包括比采用其它交通方式乘客所节省的时间效益,其中工作时间效益通常以平均工资率来进行估价,非工作时间效益以该价值的一半进行估价。分析期内的出行需求根据所研究地区的交通规划按比例增加。
支付意愿(WTP)是一个用来衡量直接和间接效益的概念。对大多数的乘客来说,WTP比他们实际支付的费用高。城市轨道交通出行的WTP可以利用标准出行模型来估计。间接效益的WTP可用条件评价法[10]来分析。
2.2政策评价理论
交通项目评价在重视项目经济效益的同时,应从福利经济学的概念和原理出发进行分析。除了评价项目在经济方面的影响外,还必须评价非经济方面的影响,例如,城市人口分布的合理性、政治上的公平性,这些可能难以定量计算,可以采用比较性的、描述性的文字或表格来定性说明。其中一些比较重要的影响因素要提交专家讨论,经确认后可以作为项目方案设计的约束条件来看待,例如重要场所周围的空气质量、历史遗址的保护等。
够定量分析时,需要进行盈亏分析及不确定性分析。因为很多预测数据往往与实际差异很大。例如,上个世纪80年代对北美已建的轨道交通系统的客流预测进行了评价,发现预测值高出或低于实际值至少10%,还有一些高出30%甚至更多[11].1984年Gordon等人采用回归方程对世界各国城市轻轨客流预测结果误差做了较系统的分析,发现客流预测值普遍偏高[12].
3UMTA采用的评价方法
3.1UMTA(1976-1978)评价规则UMTA(1976)项目评价规则于1976年正式使用。该规则把经济效果看作是费用-效益评价分析的理论基础,明确地提出了多种成本和效率水平的评价指标,其中效率通过“总体目标”和“局部目标”两方面来量度[13],总体目标没有分层次,不可计量,也没有进行国民经济效益的评价。因此在1978年,UMTA依据联邦政府的“城市轨道交通发展政策”修订了1976年的评价规则,它规定联邦政府轨道交通发展基金只分配给“人口稠密且具有明确的市中心区的城市”(一般指那些“较古老的市中心”)。同时,申请财政援助的城市必须提交一份财政规划和支持交通运输的措施,例如车站附近地区的停车政策,在中央商务区(CBD)的汽车限制。考虑到方案比较时的不确定性,1978年的UMTA评价方法规定:“申请者必须清楚地说明交通设施进行部分或全部立体交叉的必要性。这就意味着,如果有一个常规公交方案在主要性能上与轨道交通方案差不多,那么常规公交”方案将会被选中。轨道交通方案要获得支持必须提供更有力的证据[14].
1978年UMTA评价方法仍然有其不足之处。例如,在1983年对加利福尼亚萨克拉门托的轻轨项目的评价实践中[14],尽管使用了节约能源、加速经济增长等指标,但这些指标难以定量化,这使得评价者对某些指标的实际作用模糊不清,因人而异。UMTA看重规划年度单位乘客的年平均总成本,该指标偏好于高架方案;当地城市规划者则倾向于使用规划年度的年总运营和维修成本,该指标偏好于轻轨方案。
3.2UMTA(1984)评价规则
UMTA(1984)评价规则是1984年修订的,该方法引入福利经济学的概念,采用边际评价,其评价规则涉及:成本-效率、地方财政的支持、私营部门的参与、方案定量分析结果、亏损行业的参与、地方政府的支持。在评价前期,该方法通过设置约束条件排除一些明显较差的方案,这些约束也包括政治方面的因素。在评价后期的方案选择时,该方法把国会发布的有关标准合成了一个综合指标,以便能对项目进行明确的等级划分[15].
项目评价过程分为三轮。在第一轮评价中,轨道交通备选方案必须满足两项必要条件。一是线路的单向高峰小时最高断面流量至少达到1.5万人次,二是被评价项目每日每乘次的出行成本不大于10美元。10美元大约是一个公共汽车乘客改乘轨道交通后平均节省的社会效益的3倍。人均出行成本有两种算法:①每日每乘客的工程投资、运营及维修成本和乘客的旅行时间成本之和,即为“总成本-效率”(CE)指标;②上述总成本中除去当地政府投资成本,即为“联邦政府的成本-效率”(FCE)指标。
在第二轮评价中,轨道交通项目必须满足下面三项条件:①相对于公共汽车方案来说,轨道交通项目引起公交客运总量的增加;②在已有的备选方案中,推荐方案的每个乘客的成本最小;③该项目每日每个新增乘客的联邦政府的成本应不大于6美元。
在第三轮评价中,根据CE及FCE将项目分成高、中、低3个等级。CE及FCE指标都较大的方案归入高等级,两种指标都不高的方案归入低等级,其它情况归入中等级。
为了提高推荐方案的等级,当地政府会设法提高当地融资的匹配条件,该条件可以降低每个新增乘客的FCE,提高其评价等级。同样,如果当地的运营维修成本能通过税收或其它途径来保证,方案的评价等级也可提高。另外,当地的汽车停车和限制政策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提高轨道交通项目的评价等级。
这套评价规则的一个明显特点是将轨道交通项目引起的新增乘客看作是某种经济利益。它认为每增加一个新乘客,就意味着轨道交通向社会作出了将近6美元的社会效益。这种度量方法是以估计所节省的时间成本及汽车行驶成本为基础的,由此估算出乘客的支付意愿。
该方法用于政策分析有不少优点:评价标准减少;对它们的限制条件的减少;通过三个阶段的评价来处理不确定性因素;它是一个合理的、全面的费用-效率法。这种方法最后归结为一个指标来选择方案,使得方案比选易于操作。但是,这种方法在某些方面还存在一些缺点,例如对每位新增乘客成本及乘客支付意愿的确定方法还不能令人信服,有些规则仍然有一定的模糊性。
3.3UMTA(1986)评价规则UMTA于1986年发布更加完善的评价规则(一本手册),这又使评价方法进了一步。该方法补充了乘客的支付意愿的评价标准[16],还对效益、成本的定义和指标都进行了标准化。为了减少各城市在客流预测方面弄虚作假带来的影响,该规则加强了对需求预测模型的检查和限制,对项目运营维修成本的范围也做了规定。为了消除重复计算,对土地价值的增加、出行成本的减少等作了区分。该手册同时强调,如果项目是有效益的,即使公共客流量减少,联邦政府也可以对其进行拨款。这套规则最明显的改进之处就是基于出行预测模型的数据对估算出行效益的支付意愿进行确定。在评价指标方面还有一些需改进之处:更精确地定义了时间成本;独立计算方案的外部效应,而不是假定它们与直接效益成比例;为各城市的支付意愿调查推荐了一种标准方法。
这种方法引入了一些有用的政策分析概念,使人们可以更全面地进行分析。此外还在分析指标中,加入决策过程中的一些非指标数据的分析,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影响项目的等级划分。这是一个有用的框架结构,考虑了非经济信息的作用。该方法承认规则中的不确定性,但是没有考虑实际评价中的不确定性,这会导致在项目评价中产生不良影响。
4结语
(1)UMTA把成本-效率作为最重要的评价指标,而不是去度量项目的经济效益。应该尽可能去评价包括间接成本和效益在内的社会经济效益,改善其实用性。
(2)如果对空气污染、交通拥挤阻塞和其它间接影响能够以公平的方式实行货币化估算,那么就可以对非经济方面的影响进行权衡分析。这样可以让决策者更全面地进行项目的决策。UMTA应当使用均衡分析法,对项目非经济方面的影响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
(3)不确定性和偏差。评价指标涉及多方面的因素,如何减少这些因素的不确定性对评价结果的正确性有重要意义。评价中的一些关键数据,如预测客流量、运营及维修费用等,其数据往往有较大偏差,如何减少这些因素的影响对改善决策的正确性也是很重要的。在我国近阶段的城市轨道交通建设中,需要借鉴国外经验逐渐完善项目评价方法,确保所推荐的建设项目具有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这样才能维持和促进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各类企业等多方面的资本投入城市轨道交通建设,尽快改善我国的城市交通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