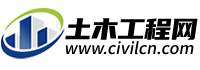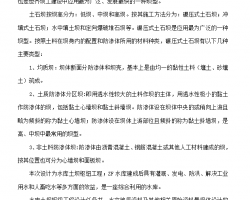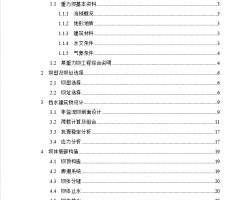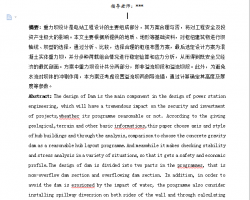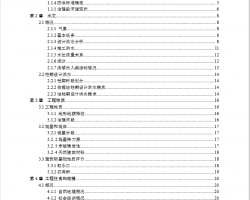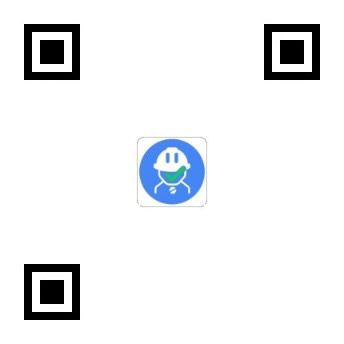摘 要 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发生了重大变化,特别是农地流转制度的确立,导致农地利用市场的初步形成,国家政策不断做出调整和让步,但其应急权宜色彩明显,不仅使农民的利益处于不确定状态,也使农村土地市场的形成缺乏法律保障,建立规范的农地使用权制度,尤其是农地使用权的物化权是解决问题的根本。
关键词 农地使用权 规范制度 物权化
一、农地使用权的概念
依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法律确定了“土地承包经营权”概念。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在农业用地上为农业目的而设定的使用权,是在较长期限内为进行农业生产或经营(诸如种植、养殖、畜牧等)而排他性的使用国有或集体所有的土地的权利豍。土地承包经营权实为一种使用权而非经营权豎。而“承包”仅是该使用权取得的一种方式,故改称“土地使用权”较为合适。但土地使用权通常指国有土地使用权。有学者依据农地的农用性质并据此与农村宅地使用权相区分,设想“农地使用权”的法律概念,并做如下定义:
以种植、养殖、畜牧等农业目的,对国家或集体所有的农用土地占有、使用、收益的权利豏。
依这一定义,农地使用权人无权处分农地。农地使用权是一种他物权,受所有权限制,不能对物之所有进行处分。然而实践中出现并得到国家默认的“反租倒包”豐现象意味着承包人有权处分农地。
该民事关系得以发生的前提是承包人有转让对农地的占有使用的意思表示,而非发包人的许可或要求。发包人作为承包关系的一方当事人无权许可更无权要求一方依某种意思去行为,承包人相对与发包人是完全的意思自治。在立法上,依《民法通则》第八十一条和《保护条令》第十二条规定,农业集体经济组织作为集体土地的使用权人可将农地发包给个人或集体组织,这说明农地使用权人有权对农地进行利用层次上的处分,只要这种处分不危机所有权的归属和并不冲破所有权对使用权的限制。
从充分利用农地的角度来看,在农地的所有权相对固化的情况下,只有赋予使用权人移交农地并为他人设定农地使用权的处分权,才有可能实现农地的优化利用。因此,农地使用权应当包含一定的处分权能。
综上所述,农地使用权是以种植、养殖、畜牧等农业目的,对国家或集体所有的农地占有、使用、收益并可作有限处分的权利。
二、层层设立农地使用权的法理依据
依物权法定原则,不仅物权名称法定,而且物权内涵法定。农地使用权人为他人设立农地使用权,原权与新权显然不是同一权利,尤其在权利内容上会有较大的出入。原权利人之所以能够为他人设立新权利,其原因首先在于,权利人有权在权利范围内处分农地,而这种处分意味着权利的行使并导致权利内容主要是农地面积、使用期限的变化;其次,物权内涵法定,但法律并不禁止物权人以约定的方式来限制自己的权利。如此,则通过这种方式的新物权自然会得到法律的承认。而且,由于新物权是原物权的自我限制的结果,新物权在内涵上不会突破原物权;再次,原物权人的处分若不使其权利全部归于灭失,则必与其处分行为相应的产生一项物上的请求权。如农地使用权对农地做出租之处分,则至租赁期限届满即承租人权利行使完毕之时,出租人有权请求承租人返还土地。承租人主动返还土地之行为并不是履行义务的表现(如果当事人没有相应的规定),因为承租人只有应出租人的请求返还农地的义务,而无主动返还土地的义务;最后,“一物一权”原则目的在于防止针对同一物的各权利人之间发生权利冲突。依前述的三点原因,不同的农地使用权人之间的权利界限明确,不会导致权利冲突。
某物权若无处分权能,则该物权只能由物权人本人行使或放弃(包括怠于行使),因而不能确保对物权进行充分利用。赋予其处分权能则他人可能依据物权人的某种处分获得相应物权,从而实现对物的多主利用和流转利用。从这一点看,法律也应当赋予农地使用权人一定的处分权,这也是农地使用权依民事关系流转的前提。
三、农地使用权的物权化
承包经营权不是完全意义上的物权,其原因并不在于承包经营权的对世效力不足,承包合同、权利登记、承包人对农地的占有利用基本上排斥了第三人的非法干涉;而在于承包人对农地的支配力不足,承包经营权作为一种他物权受土地所有权的限制过严。如:承包认可以依法转让农地,但能否转让取决于承包人的许可;发包人协助贯彻土地用途管制政策并据此强制推行地方政府对农业结构性调整;承包人无权放弃农地,承包人能否退包一方面取决于发包人的同意,另一方面退包需要有法定事由,因不能退包而导致的土地荒芜或粗放型经营又构成承包人的违约事由。形成上述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承包经营权由承包合同设定并依合同行使,物权依债权设立,物权与债权始终相结合,物权的自主行使实际上成了履行合同的主要途径,不行使即导致不履行;其次,作为承包人的成员对代表行使集体土地所有权的集体组织约束不够。集体组织受民主讨论通过的土地发包方案约束,但他同时又是方案的执行者;第三,集体组织因人事方面的原因不得不代行使一定的行政管理职能。因此,有时他并不是一个遵守平等自愿原则的民事主体。
针对上述原因,强化农地使用的物权性,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一)赋予农地使用权人对农地的处分权
正如前文所述,这种处分只是利用层面上的处分,如转让、出租、抵押、入股等,该处分权有为第三人设定使用权的效力。对处分权还应有以下理解:
某种物权包含处分权能,则权利人有权依法处分权利客体。这种处分是对权利客体的处分,而不是对权利自身的处分。由于处分意味着对权利的行使,若依后一种理解则意味着,物权的行使是对物权自身的行使。行为的依据同时成了行为的对象,于理不通。处分物权客体可导致新物权的产生,如出让土地则由土地所有权衍生出土地使用权;转让、出租土地,则新的土地使用权产生。新物权的产生或是对原物权权能的继受或是对这些权能的分割整合。由此又可作如下论断:权利可以量化,而且,一项权利经权利人以及通过一定的法律关系得以行使该权利之部分或其衍生权利的人的行使,最终会消耗殆尽,被行使的权利的总和总是少于或等于原有权利的总量。转让、出租农地实质上是农地使用权人对其所享有的权利在时间、空间和权能即权利内容上进行量的析解整合,因而不会突破原权利的范围。 (二)完善农地使用权登记
在我国,登记不动产物权的公示方式,农地使用权应当进行登记。然而,登记究竟是一种公法义务还是一种私法行为?笔者认为应是一种私法行为。从物权人的角度来看,不申请不动产登记并不直接导致一定的法律后果,在此意义上是否登记取决于物权人的意志。从登记机关的角度看,登记机关只有履行如实登记的义务,而无权也不可能强迫不动产物权人申请登记。不动产物权人不申请登记的,登记机关不可对其作任何处分。
登记有确认不动产物权的归属并据以排斥他人非法干涉的效能。农地使用权人从自身利益出发,应积极主动的申请农地使用权的登记,以确认和维护自己的权利。完善农地使用权登记制度的意义在于确认农地使用人的使用权,这种确认的排他作用主要应针对农地所有人。如前所述,通过合同、登记、占有基本排斥了第三人的干涉,而对农地所有人的约束显得还不够。完善农地使用权的登记,应进一步明确农地使用权的具体内容。而不是只作笼统的登记。
(三)农地使用权和农地利用合同的分离运作
“承包权与承包合同的分离运作,符合物权行为抽象性规则”。合同的签订意味着债权的成立,进行农地使用权的登记始成立物权关系。农地利用合同的变更并不必然引起农地使用权的变更不可避免,应当允许当事人之间协商调整,这种调整仍是双方当事人的合意,可以看作原合同的续签,不过这种续签并不必然涉及合同的期限。农地利用合同变更的,应当作相应的农地使用权变更登记。这样形成农地使用权与农地利用权既相互关联又相互独立的法律关系,即发生物权关系和债权关系。
(四)明确村民委员会对村干部的制约关系
村干部是享有一定行政管理职权的村务管理人员(不包括村民委员会成员)。村干部进行行政管理不应与村民委员会的决议相冲突。首先,村干部和村民委员会成员都是由村民以民主的方式产生,都是民意的结果。因此,他们的行为都应是民意的体现,不存在谁制约谁的问题。其次,村干部的权力是乡(镇)行政权的下放,而这种权力一旦下放,其效力范围仅限于村;村的最高决策机构是村民会议,村民委员会是村民会议的常设机构和权力行使者,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村民委员会又可以制约村干部的行政职权。
村民委员会签订农地利用合同,其在合同中的意思应视为村民委员会的决议,村干部无权介入、干预该合同关系。这样,在农地利用上排斥基层行政力量的干预,保护农地使用权人的权利。
四、农地使用权的取得和消灭
农地使用权可以依合同取得,也可依占有取得。《管理法》第四十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可依法确定国有荒地开发人的使用权。这种“确定”,实质上应是权利确认,开发人早已占有使用国有荒地,只不过权利未得到国家的确认而已。一旦确认开发人的权利,其效力应溯及至开发人开始占有该荒地之时。否则,开发人对未确认之前的开发所产生的就无权享有,这显然与事实不符。
农地使用权的消灭原因:(1)农地使用权期限届满;(2)农地使用权的抛弃;(3)农地使用权的撤销;(4)国家征收土地;(5)土地规划;(6)土地灭失等。
我国正处在政治经济体制的转型时期,面临着众多需要解决的问题,而农村中的问题,特别是农地使用权流转的问题尤为突出,应引起高度重视。本文仅是笔者就农地使用权制度的确立进行浅析及初探,藉以引起更多人的重视。
注释:
梁彗星主编.中国物权法研究.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
彭万林主编.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91页,第292页.
“反租倒包”指:发包人租赁已承包给承包人的农地并再予以发包(实质是转让)的行为。
关键词 农地使用权 规范制度 物权化
一、农地使用权的概念
依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法律确定了“土地承包经营权”概念。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在农业用地上为农业目的而设定的使用权,是在较长期限内为进行农业生产或经营(诸如种植、养殖、畜牧等)而排他性的使用国有或集体所有的土地的权利豍。土地承包经营权实为一种使用权而非经营权豎。而“承包”仅是该使用权取得的一种方式,故改称“土地使用权”较为合适。但土地使用权通常指国有土地使用权。有学者依据农地的农用性质并据此与农村宅地使用权相区分,设想“农地使用权”的法律概念,并做如下定义:
以种植、养殖、畜牧等农业目的,对国家或集体所有的农用土地占有、使用、收益的权利豏。
依这一定义,农地使用权人无权处分农地。农地使用权是一种他物权,受所有权限制,不能对物之所有进行处分。然而实践中出现并得到国家默认的“反租倒包”豐现象意味着承包人有权处分农地。
该民事关系得以发生的前提是承包人有转让对农地的占有使用的意思表示,而非发包人的许可或要求。发包人作为承包关系的一方当事人无权许可更无权要求一方依某种意思去行为,承包人相对与发包人是完全的意思自治。在立法上,依《民法通则》第八十一条和《保护条令》第十二条规定,农业集体经济组织作为集体土地的使用权人可将农地发包给个人或集体组织,这说明农地使用权人有权对农地进行利用层次上的处分,只要这种处分不危机所有权的归属和并不冲破所有权对使用权的限制。
从充分利用农地的角度来看,在农地的所有权相对固化的情况下,只有赋予使用权人移交农地并为他人设定农地使用权的处分权,才有可能实现农地的优化利用。因此,农地使用权应当包含一定的处分权能。
综上所述,农地使用权是以种植、养殖、畜牧等农业目的,对国家或集体所有的农地占有、使用、收益并可作有限处分的权利。
二、层层设立农地使用权的法理依据
依物权法定原则,不仅物权名称法定,而且物权内涵法定。农地使用权人为他人设立农地使用权,原权与新权显然不是同一权利,尤其在权利内容上会有较大的出入。原权利人之所以能够为他人设立新权利,其原因首先在于,权利人有权在权利范围内处分农地,而这种处分意味着权利的行使并导致权利内容主要是农地面积、使用期限的变化;其次,物权内涵法定,但法律并不禁止物权人以约定的方式来限制自己的权利。如此,则通过这种方式的新物权自然会得到法律的承认。而且,由于新物权是原物权的自我限制的结果,新物权在内涵上不会突破原物权;再次,原物权人的处分若不使其权利全部归于灭失,则必与其处分行为相应的产生一项物上的请求权。如农地使用权对农地做出租之处分,则至租赁期限届满即承租人权利行使完毕之时,出租人有权请求承租人返还土地。承租人主动返还土地之行为并不是履行义务的表现(如果当事人没有相应的规定),因为承租人只有应出租人的请求返还农地的义务,而无主动返还土地的义务;最后,“一物一权”原则目的在于防止针对同一物的各权利人之间发生权利冲突。依前述的三点原因,不同的农地使用权人之间的权利界限明确,不会导致权利冲突。
某物权若无处分权能,则该物权只能由物权人本人行使或放弃(包括怠于行使),因而不能确保对物权进行充分利用。赋予其处分权能则他人可能依据物权人的某种处分获得相应物权,从而实现对物的多主利用和流转利用。从这一点看,法律也应当赋予农地使用权人一定的处分权,这也是农地使用权依民事关系流转的前提。
三、农地使用权的物权化
承包经营权不是完全意义上的物权,其原因并不在于承包经营权的对世效力不足,承包合同、权利登记、承包人对农地的占有利用基本上排斥了第三人的非法干涉;而在于承包人对农地的支配力不足,承包经营权作为一种他物权受土地所有权的限制过严。如:承包认可以依法转让农地,但能否转让取决于承包人的许可;发包人协助贯彻土地用途管制政策并据此强制推行地方政府对农业结构性调整;承包人无权放弃农地,承包人能否退包一方面取决于发包人的同意,另一方面退包需要有法定事由,因不能退包而导致的土地荒芜或粗放型经营又构成承包人的违约事由。形成上述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承包经营权由承包合同设定并依合同行使,物权依债权设立,物权与债权始终相结合,物权的自主行使实际上成了履行合同的主要途径,不行使即导致不履行;其次,作为承包人的成员对代表行使集体土地所有权的集体组织约束不够。集体组织受民主讨论通过的土地发包方案约束,但他同时又是方案的执行者;第三,集体组织因人事方面的原因不得不代行使一定的行政管理职能。因此,有时他并不是一个遵守平等自愿原则的民事主体。
针对上述原因,强化农地使用的物权性,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一)赋予农地使用权人对农地的处分权
正如前文所述,这种处分只是利用层面上的处分,如转让、出租、抵押、入股等,该处分权有为第三人设定使用权的效力。对处分权还应有以下理解:
某种物权包含处分权能,则权利人有权依法处分权利客体。这种处分是对权利客体的处分,而不是对权利自身的处分。由于处分意味着对权利的行使,若依后一种理解则意味着,物权的行使是对物权自身的行使。行为的依据同时成了行为的对象,于理不通。处分物权客体可导致新物权的产生,如出让土地则由土地所有权衍生出土地使用权;转让、出租土地,则新的土地使用权产生。新物权的产生或是对原物权权能的继受或是对这些权能的分割整合。由此又可作如下论断:权利可以量化,而且,一项权利经权利人以及通过一定的法律关系得以行使该权利之部分或其衍生权利的人的行使,最终会消耗殆尽,被行使的权利的总和总是少于或等于原有权利的总量。转让、出租农地实质上是农地使用权人对其所享有的权利在时间、空间和权能即权利内容上进行量的析解整合,因而不会突破原权利的范围。 (二)完善农地使用权登记
在我国,登记不动产物权的公示方式,农地使用权应当进行登记。然而,登记究竟是一种公法义务还是一种私法行为?笔者认为应是一种私法行为。从物权人的角度来看,不申请不动产登记并不直接导致一定的法律后果,在此意义上是否登记取决于物权人的意志。从登记机关的角度看,登记机关只有履行如实登记的义务,而无权也不可能强迫不动产物权人申请登记。不动产物权人不申请登记的,登记机关不可对其作任何处分。
登记有确认不动产物权的归属并据以排斥他人非法干涉的效能。农地使用权人从自身利益出发,应积极主动的申请农地使用权的登记,以确认和维护自己的权利。完善农地使用权登记制度的意义在于确认农地使用人的使用权,这种确认的排他作用主要应针对农地所有人。如前所述,通过合同、登记、占有基本排斥了第三人的干涉,而对农地所有人的约束显得还不够。完善农地使用权的登记,应进一步明确农地使用权的具体内容。而不是只作笼统的登记。
(三)农地使用权和农地利用合同的分离运作
“承包权与承包合同的分离运作,符合物权行为抽象性规则”。合同的签订意味着债权的成立,进行农地使用权的登记始成立物权关系。农地利用合同的变更并不必然引起农地使用权的变更不可避免,应当允许当事人之间协商调整,这种调整仍是双方当事人的合意,可以看作原合同的续签,不过这种续签并不必然涉及合同的期限。农地利用合同变更的,应当作相应的农地使用权变更登记。这样形成农地使用权与农地利用权既相互关联又相互独立的法律关系,即发生物权关系和债权关系。
(四)明确村民委员会对村干部的制约关系
村干部是享有一定行政管理职权的村务管理人员(不包括村民委员会成员)。村干部进行行政管理不应与村民委员会的决议相冲突。首先,村干部和村民委员会成员都是由村民以民主的方式产生,都是民意的结果。因此,他们的行为都应是民意的体现,不存在谁制约谁的问题。其次,村干部的权力是乡(镇)行政权的下放,而这种权力一旦下放,其效力范围仅限于村;村的最高决策机构是村民会议,村民委员会是村民会议的常设机构和权力行使者,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村民委员会又可以制约村干部的行政职权。
村民委员会签订农地利用合同,其在合同中的意思应视为村民委员会的决议,村干部无权介入、干预该合同关系。这样,在农地利用上排斥基层行政力量的干预,保护农地使用权人的权利。
四、农地使用权的取得和消灭
农地使用权可以依合同取得,也可依占有取得。《管理法》第四十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可依法确定国有荒地开发人的使用权。这种“确定”,实质上应是权利确认,开发人早已占有使用国有荒地,只不过权利未得到国家的确认而已。一旦确认开发人的权利,其效力应溯及至开发人开始占有该荒地之时。否则,开发人对未确认之前的开发所产生的就无权享有,这显然与事实不符。
农地使用权的消灭原因:(1)农地使用权期限届满;(2)农地使用权的抛弃;(3)农地使用权的撤销;(4)国家征收土地;(5)土地规划;(6)土地灭失等。
我国正处在政治经济体制的转型时期,面临着众多需要解决的问题,而农村中的问题,特别是农地使用权流转的问题尤为突出,应引起高度重视。本文仅是笔者就农地使用权制度的确立进行浅析及初探,藉以引起更多人的重视。
注释:
梁彗星主编.中国物权法研究.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
彭万林主编.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91页,第292页.
“反租倒包”指:发包人租赁已承包给承包人的农地并再予以发包(实质是转让)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