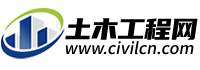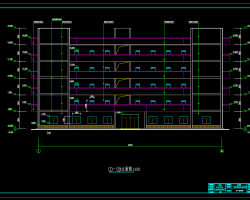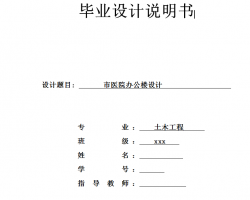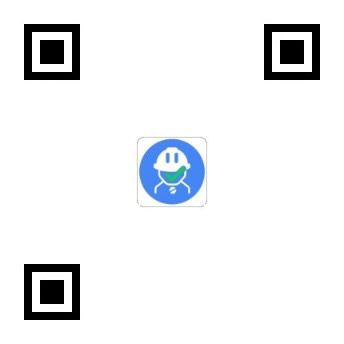有一种历史很悠久的说法:建筑是一门艺术。近来的说法是:建筑是一种生产,艺术也是生产。那么,以生产力来作为标准衡量建筑,合适吗?已故意大利新左派建筑历史学家M·塔非里说,建筑史家和批评家在建筑理论中的作用,就好象在皇家宴会开筵以前就提议为国王祝酒的一位穿着华丽的笨伯。他意在指责传统的历史学家已成不合时宜的向文化延续性打恭作揖的"保守派"。这可以看作是现代主义建筑运动在本世纪风起云涌之时,先锋派建筑大师和理论家代表所谓"生产阶级"对传统的保守的知识分子尖酸刻薄的攻击。
而在中国,建筑界的情况与欧洲有所不同。各大专院校、研究所内领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之职的专家教授们,大多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推崇者,因而他们对于现代主义建筑运动的先锋派理论之译介、宣扬乃不遗余力,甚至很有一般子借此在建筑界反封建(权威、迷信等)的气势。而那些处于"生产第一线"的建筑师们,反而由于视野的闭塞,对人文知识的隔膜,在建筑创作中处于一种封闭、保守和势利眼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建筑首先是一种生产"、"生产力是一个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等由浅入深、由具体到抽象的说法,只是简约为口号标签时,"生产者"就被建筑师拿来贴在自己的大旗上,以与理论家、历史学家、批评家分开阵营。并且,由于挟意识形式之余威,"生产者"似乎要比"非生产者"、"不劳而获的批评家"高贵得多--确实,因为国家建筑业的蓬勃发展,巨额金钱在房地产、建筑业运转,处于"生产第一线"的建筑师斩获甚多,财一大,气也粗,身份儿也就"高贵"起来。在建筑学领域,按照这么一个可疑的标准把建筑和理论家、批评家分了等级贵贱,建筑批评还有谁去说?怎么说?
但是,建筑批评确实必须进行,不能将这一神圣之职简单地让与"使用者"和"业主",或者让"时间"。批评家并不是很容易就让"教师"、撰文介绍自己的设计的建筑师或者专业杂志的编辑顶其头衔的。"教师"的职业,在于"传道、授业、解惑",一般不会公开发表对当下的建筑作品的批评意见,更难以形成系统的批评理论。撰文作自我作品介绍的建筑师,既不敢冒犯其他建筑师,也不敢将自己的理论(如果说有的话)张扬,总是一口温吞水。好在中国传统语文中的许多温文尔雅言辞之后的傲岸与硬气还是能让人感觉行到,但总够不上建筑批评的文法。一般的杂志编辑,则只好以不偏不倚的"执事"为己任,批评的矛头,只能略存于文章取舍之间。如是说未,在建筑学术圈内,竟没有多少批评余地了。我们在书刊上也见过几场笔墨官司,除了七十年代以前的"民族形式、社会主义内容"曾剑拨努张,实际上也不过是政治帽子互相扣的游戏之外,八十年代以来的建筑领域的争论,却竟象观摩一场场太极推手,彼此用"气",尽管当局者可能心神领会、惊心动魄,却实在构不成有概念和范畴可循的批评法则。
建筑批评家应该是博览群书、通晓历史和人文学科理论的人。古罗马维特鲁威对建筑师的期望是:"建筑师应该擅长文笔,熟习制图,精通几何,深悉各种历史,勤听哲学,理解音乐,对医学并非茫然无知,通晓法律家的著述,具备天文学或天体理论的知识。"这倒似乎更适合于对一个建筑批评家的要求。那么,对于一个当代的建筑批评家来说,主要有哪些条件呢?第一,如上所述的丰富而深厚的人文知识和专业知识;第二,宗教家般的对于非物质利益--批评事业、批评艺术的热忱。
而在中国,建筑界的情况与欧洲有所不同。各大专院校、研究所内领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之职的专家教授们,大多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推崇者,因而他们对于现代主义建筑运动的先锋派理论之译介、宣扬乃不遗余力,甚至很有一般子借此在建筑界反封建(权威、迷信等)的气势。而那些处于"生产第一线"的建筑师们,反而由于视野的闭塞,对人文知识的隔膜,在建筑创作中处于一种封闭、保守和势利眼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建筑首先是一种生产"、"生产力是一个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等由浅入深、由具体到抽象的说法,只是简约为口号标签时,"生产者"就被建筑师拿来贴在自己的大旗上,以与理论家、历史学家、批评家分开阵营。并且,由于挟意识形式之余威,"生产者"似乎要比"非生产者"、"不劳而获的批评家"高贵得多--确实,因为国家建筑业的蓬勃发展,巨额金钱在房地产、建筑业运转,处于"生产第一线"的建筑师斩获甚多,财一大,气也粗,身份儿也就"高贵"起来。在建筑学领域,按照这么一个可疑的标准把建筑和理论家、批评家分了等级贵贱,建筑批评还有谁去说?怎么说?
但是,建筑批评确实必须进行,不能将这一神圣之职简单地让与"使用者"和"业主",或者让"时间"。批评家并不是很容易就让"教师"、撰文介绍自己的设计的建筑师或者专业杂志的编辑顶其头衔的。"教师"的职业,在于"传道、授业、解惑",一般不会公开发表对当下的建筑作品的批评意见,更难以形成系统的批评理论。撰文作自我作品介绍的建筑师,既不敢冒犯其他建筑师,也不敢将自己的理论(如果说有的话)张扬,总是一口温吞水。好在中国传统语文中的许多温文尔雅言辞之后的傲岸与硬气还是能让人感觉行到,但总够不上建筑批评的文法。一般的杂志编辑,则只好以不偏不倚的"执事"为己任,批评的矛头,只能略存于文章取舍之间。如是说未,在建筑学术圈内,竟没有多少批评余地了。我们在书刊上也见过几场笔墨官司,除了七十年代以前的"民族形式、社会主义内容"曾剑拨努张,实际上也不过是政治帽子互相扣的游戏之外,八十年代以来的建筑领域的争论,却竟象观摩一场场太极推手,彼此用"气",尽管当局者可能心神领会、惊心动魄,却实在构不成有概念和范畴可循的批评法则。
建筑批评家应该是博览群书、通晓历史和人文学科理论的人。古罗马维特鲁威对建筑师的期望是:"建筑师应该擅长文笔,熟习制图,精通几何,深悉各种历史,勤听哲学,理解音乐,对医学并非茫然无知,通晓法律家的著述,具备天文学或天体理论的知识。"这倒似乎更适合于对一个建筑批评家的要求。那么,对于一个当代的建筑批评家来说,主要有哪些条件呢?第一,如上所述的丰富而深厚的人文知识和专业知识;第二,宗教家般的对于非物质利益--批评事业、批评艺术的热忱。
批评家和纯粹学术的研究者有所不同。纯粹学术的研究,可能根本无助于当下的建筑事业,但他们的研究成果也许是研究者个人爱智与求真的知识产品。求真本身的价值就足以便人迷醉。历史上有许多为纯学术而献身的人们,并不会因为其成果没有当下的实用价值而失去其光芒。恰恰相反,如果说他们有大用的话,他们是批评家头上的灯塔,民众仰目的星辰。但批评家必须在社会的现实层面上运作,成为建筑作品与意义的联结者和批判者,他们要影响建筑师和公众。后现代理论有所谓"双重译码",其中包括建筑的意义向建筑师和公共两个层次敝开。但批评家有第三者的声音,第三译码。后现代文化遭到解构之虞,也就是要加上批评家这一旁观者和阐释者。批评家的参与是历史的,又是当下的:是个人的,又是社会的;是综合的、又是分析的。
批评家和建筑师的分工不同,在于建筑师使用的建筑语言可以是跳跃的。片断的和拼贴的(这也是艺术创作的共通性),而批评家必须用合乎逻辑的语言,将拼贴的建筑的意义粘接到公共语言之中。当然从广义来说,每一个人都可以以自己的方式领会建筑的意义,但社会的行业发展和公共交流的环境与规模,需要一定量的专业批评的规范文本,这就要求专业的建筑批评家的存在。建筑业的发展,除了技术与行为科学上的统计信息的反馈,更重要的是作为意义阐释者的批评文本的流通。
西方历史上的人文主义建筑批评家,大多是从对经典著作(包括建筑作品)的批评,演化出一系列较为规范的形式与准则。例如,对建筑构式、建筑型制及其社会意识形态的批评。那些批评对古典的(异于基督教的)建筑语言、法则或者基督教建筑型制、场所和仪式方式的对应关系进行探索,这种以建筑形式为中心的关注,可以说是与西言皙学的形式化发展相一致的。但是,当代建筑批评受到分析哲学的影响,对社会制度、结构、心理、审美与建筑意义的关系进行挖掘、探索,拓展了建筑批评的多无化的广阔领域。
从承认人文主义传统的价值,肯定建筑史上"批判"灵魂的巨大作用这一角度,我们可以清理出批评之产生与发展的实证性的轨迹。可是,批评自身和艺术创造性都内在地存在一种反批评,即拒斥分析、批判的趋向。我们不妨以建筑的具体事例来说明这种"反批评"的存在,或许也可从一定意义上揭示建筑批评的局限性。
批评家和建筑师的分工不同,在于建筑师使用的建筑语言可以是跳跃的。片断的和拼贴的(这也是艺术创作的共通性),而批评家必须用合乎逻辑的语言,将拼贴的建筑的意义粘接到公共语言之中。当然从广义来说,每一个人都可以以自己的方式领会建筑的意义,但社会的行业发展和公共交流的环境与规模,需要一定量的专业批评的规范文本,这就要求专业的建筑批评家的存在。建筑业的发展,除了技术与行为科学上的统计信息的反馈,更重要的是作为意义阐释者的批评文本的流通。
西方历史上的人文主义建筑批评家,大多是从对经典著作(包括建筑作品)的批评,演化出一系列较为规范的形式与准则。例如,对建筑构式、建筑型制及其社会意识形态的批评。那些批评对古典的(异于基督教的)建筑语言、法则或者基督教建筑型制、场所和仪式方式的对应关系进行探索,这种以建筑形式为中心的关注,可以说是与西言皙学的形式化发展相一致的。但是,当代建筑批评受到分析哲学的影响,对社会制度、结构、心理、审美与建筑意义的关系进行挖掘、探索,拓展了建筑批评的多无化的广阔领域。
从承认人文主义传统的价值,肯定建筑史上"批判"灵魂的巨大作用这一角度,我们可以清理出批评之产生与发展的实证性的轨迹。可是,批评自身和艺术创造性都内在地存在一种反批评,即拒斥分析、批判的趋向。我们不妨以建筑的具体事例来说明这种"反批评"的存在,或许也可从一定意义上揭示建筑批评的局限性。
建筑批判理论的陈述总是不完备的,而一座建筑可以说是被完成了"客体"。倘若批评是建筑这一完整事件的继续,那么建筑批评发生在建筑这一完整的过程之中,按照现今的说法,即批评发生在建筑这一广义的文本的内部,这颇不符合人类的认知经验。所以,还是应当把建筑实体当作静止的,而解释的文本是可以涂改和变换的,它是充满变化的意义游戏。比如,建立一座教堂,当人们以狂热自觉或者执行宗教命令的方式完成它之后,对它的批评,比如它是采用了异教的罗马式圆拱,还是哥特式的在尖拱,是否体现了基督教的精神,其言辞可能热情或冷静,而批评者在情感体验和建筑意义的语言表达两个层次上,可能均难以超越设计者、建造者对建筑的体验与表达的深刻性。这可以说是建筑的硬道理,这是建筑师轻视批评家的根本原因。但是,要形成这种判断有一个前提,就是建筑师和批评家对建筑之意义探索的态度,必须是虔诚的投入。按照阐释学的理论,只有有此前提的视界融合,才可以谈论建筑这一"客体"本身的意义的完整和饱满,以及批评文本的意义变换。
建筑批评的尺码,即使如一部辞典那样齐全,与艺术创造的可能性和艺术直觉的充盈性相比,总是无穷地医乏的。所以,批评文本往往成为普洛克儒斯忒斯的铁床,成为削足适履的无奈操作。建筑批评之常常失效,原回也在于此。比如将社会的行为价值套用于一座像巴黎圣母院或者蓬皮杜文化中心之类的建筑时,我们发现建筑批评出发的逻辑起点总是处于意义飘移之中。杰出的建筑超越了历史,处于历史理念规范之中的批评家们难以对之作评价。
本世纪中叶以来,结构主义建筑批评成为一道显赫的人文景观。借助于精神分析、语言学手段,结构主义建筑批评深入了建筑的类型学和符号学的领域,并作为对现代主义先锋派建筑运动对历史批判的反动,整合进历史因素的呼声愈来愈高。建筑批评与实践,比哲学思想更为生动地体现了风水流转,批评的局限,也就充分地展现在正当的批评史上。比如按时间来说,后续的批评,总是必须去清理前人的旧战场,或者挖掘历史的沉积史料、阐发出新的妙解,在考据钩沉之间,许多批评家沉洒于故识新知,几乎没有任何批评文本对未来有足够的封闭性,成为与建筑实体一样坚固的文木。解构主义建筑批评面对的就是这样意义层次丰富多样而开放的意义世界,冗长而繁复的批评运作,很难让建筑师与大众理解与把握,因而引起了普遍的厌恶情绪。人们宁可直接欣赏建筑本身,而惮于在无穷的文字之中去追寻建筑意义的踪迹。事实上,建筑界有许多从业者是以不读书或少读书为荣的,其极端者,拒斥智者的批评,拒斥经验的指点,而直截了当走入畅快淋漓的行动中去。正如神学家保罗。蒂里希所言:"行动中的人更接近上帝。"
建筑批评的尺码,即使如一部辞典那样齐全,与艺术创造的可能性和艺术直觉的充盈性相比,总是无穷地医乏的。所以,批评文本往往成为普洛克儒斯忒斯的铁床,成为削足适履的无奈操作。建筑批评之常常失效,原回也在于此。比如将社会的行为价值套用于一座像巴黎圣母院或者蓬皮杜文化中心之类的建筑时,我们发现建筑批评出发的逻辑起点总是处于意义飘移之中。杰出的建筑超越了历史,处于历史理念规范之中的批评家们难以对之作评价。
本世纪中叶以来,结构主义建筑批评成为一道显赫的人文景观。借助于精神分析、语言学手段,结构主义建筑批评深入了建筑的类型学和符号学的领域,并作为对现代主义先锋派建筑运动对历史批判的反动,整合进历史因素的呼声愈来愈高。建筑批评与实践,比哲学思想更为生动地体现了风水流转,批评的局限,也就充分地展现在正当的批评史上。比如按时间来说,后续的批评,总是必须去清理前人的旧战场,或者挖掘历史的沉积史料、阐发出新的妙解,在考据钩沉之间,许多批评家沉洒于故识新知,几乎没有任何批评文本对未来有足够的封闭性,成为与建筑实体一样坚固的文木。解构主义建筑批评面对的就是这样意义层次丰富多样而开放的意义世界,冗长而繁复的批评运作,很难让建筑师与大众理解与把握,因而引起了普遍的厌恶情绪。人们宁可直接欣赏建筑本身,而惮于在无穷的文字之中去追寻建筑意义的踪迹。事实上,建筑界有许多从业者是以不读书或少读书为荣的,其极端者,拒斥智者的批评,拒斥经验的指点,而直截了当走入畅快淋漓的行动中去。正如神学家保罗。蒂里希所言:"行动中的人更接近上帝。"